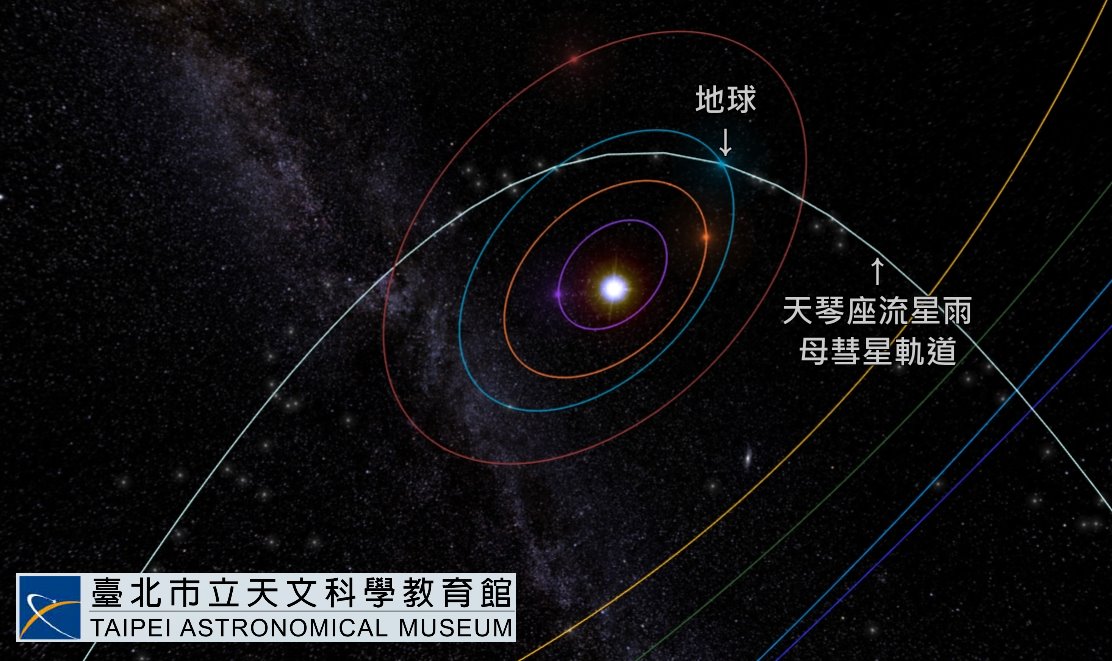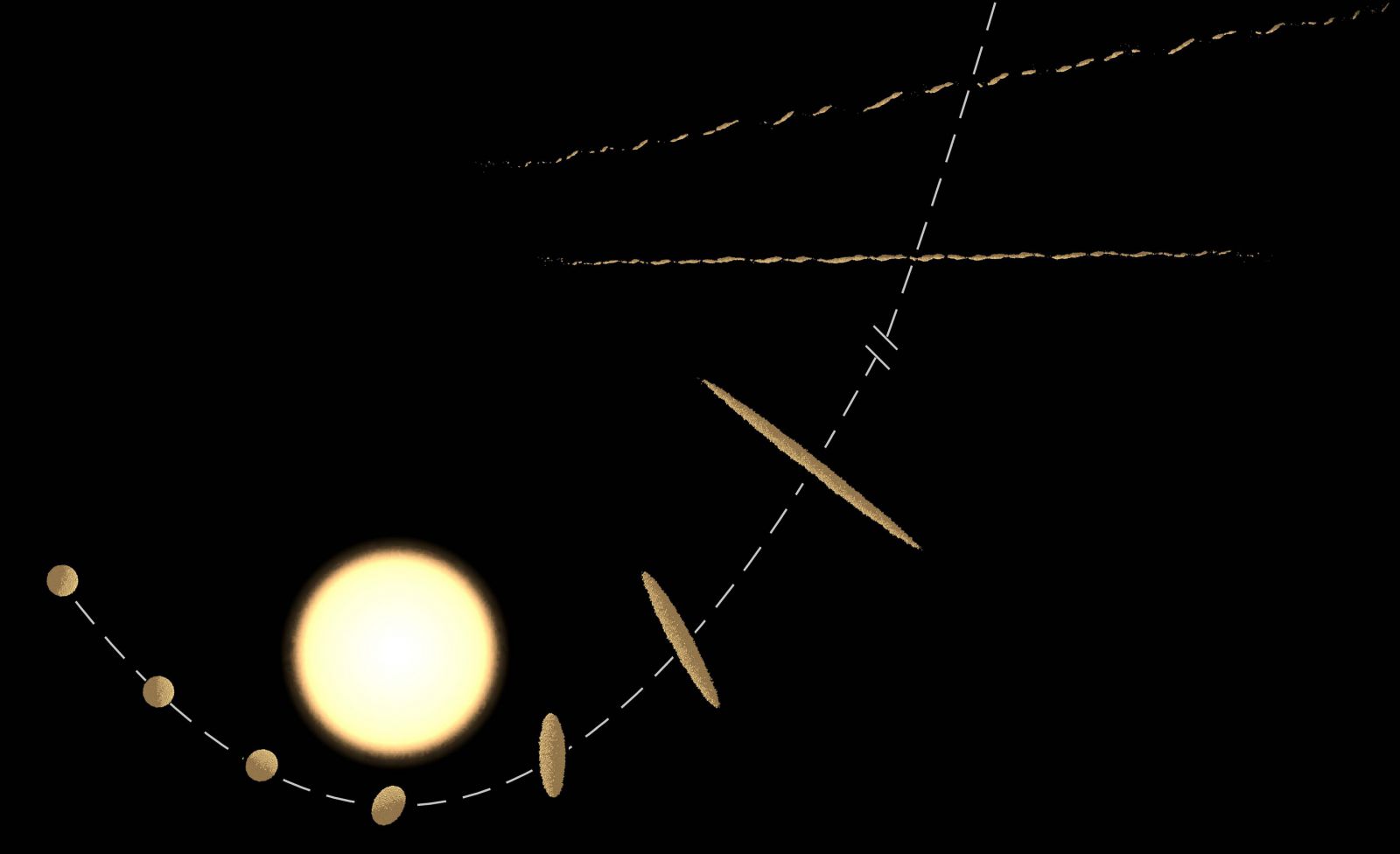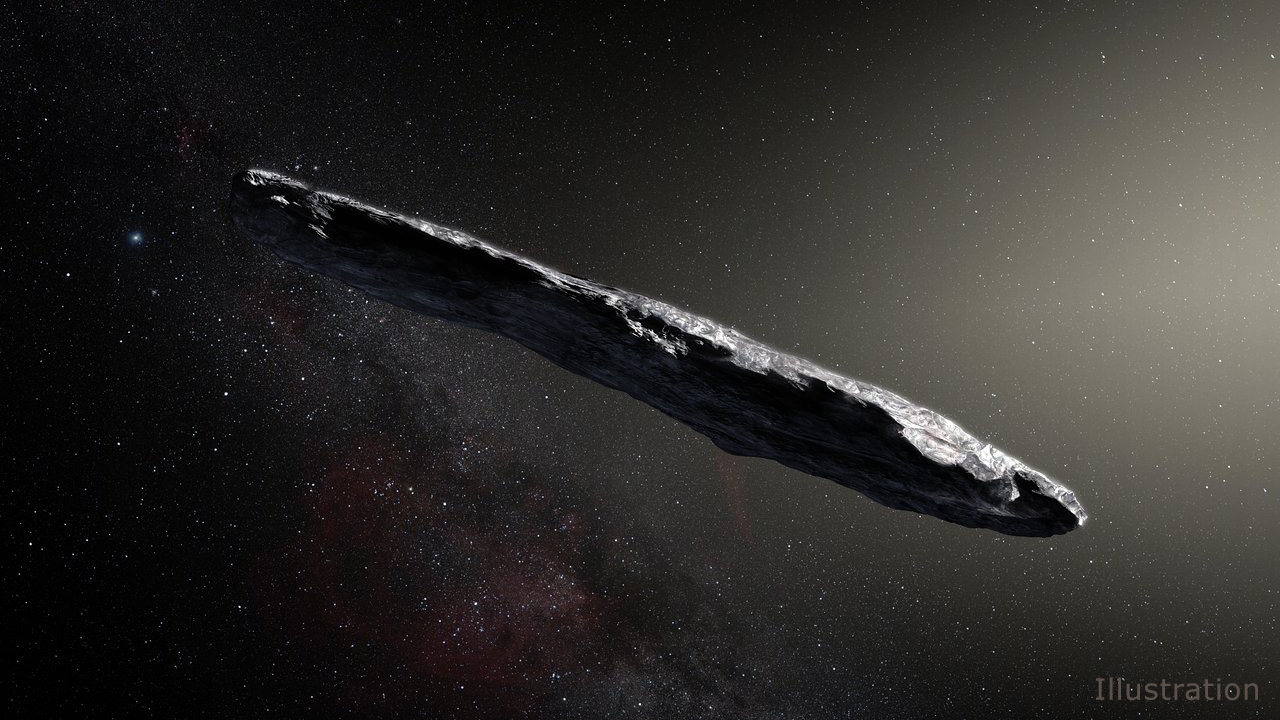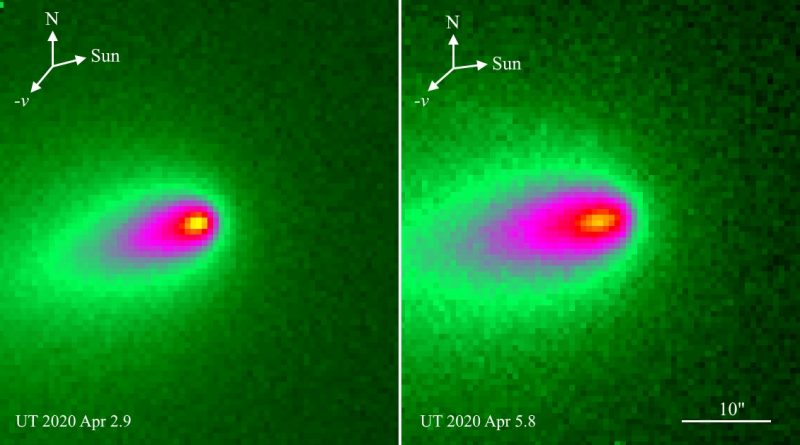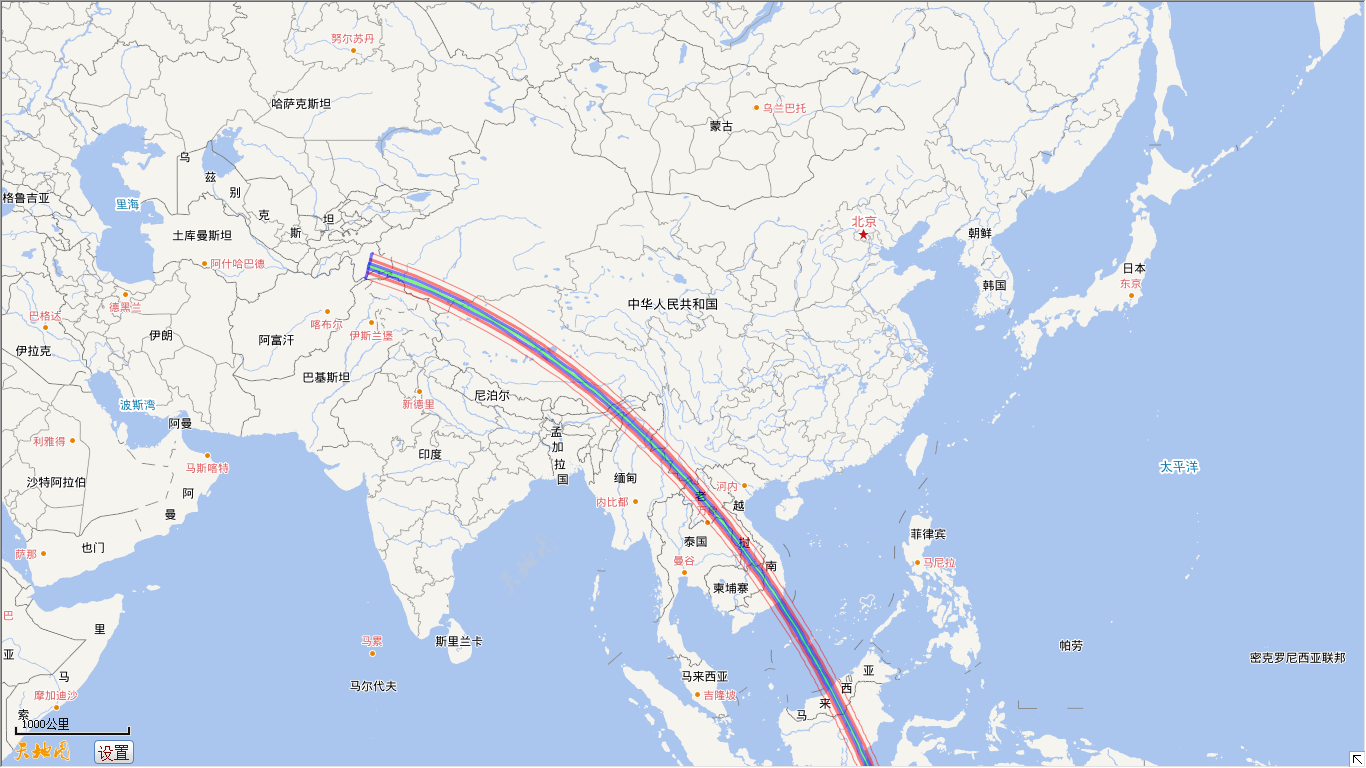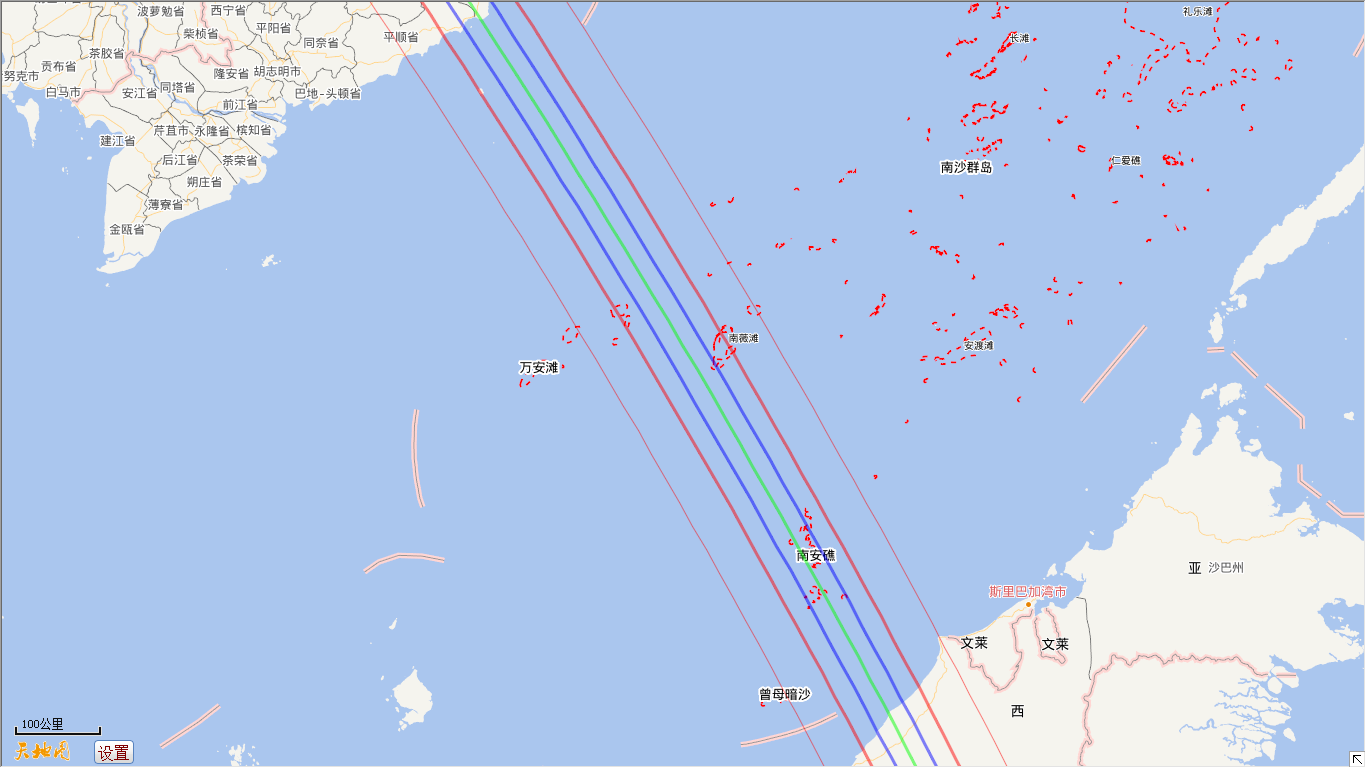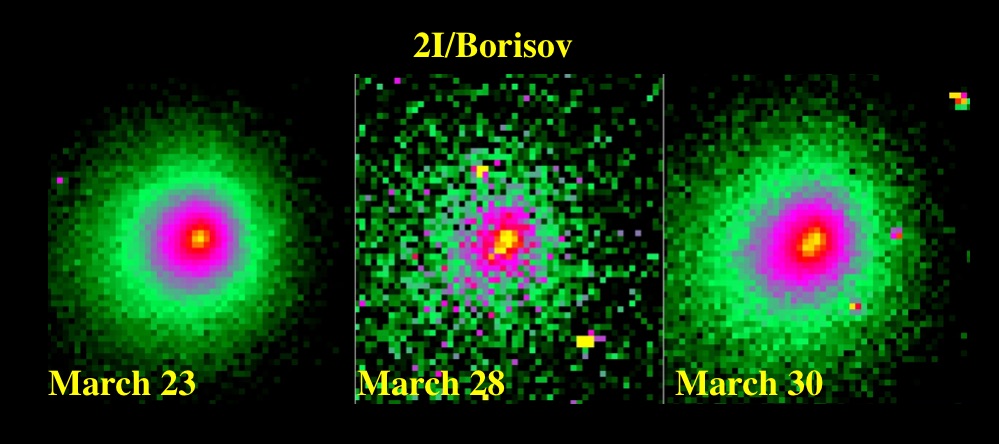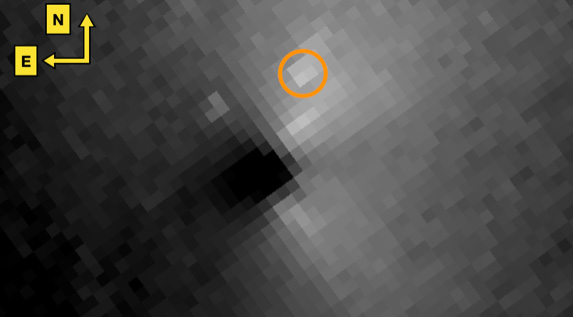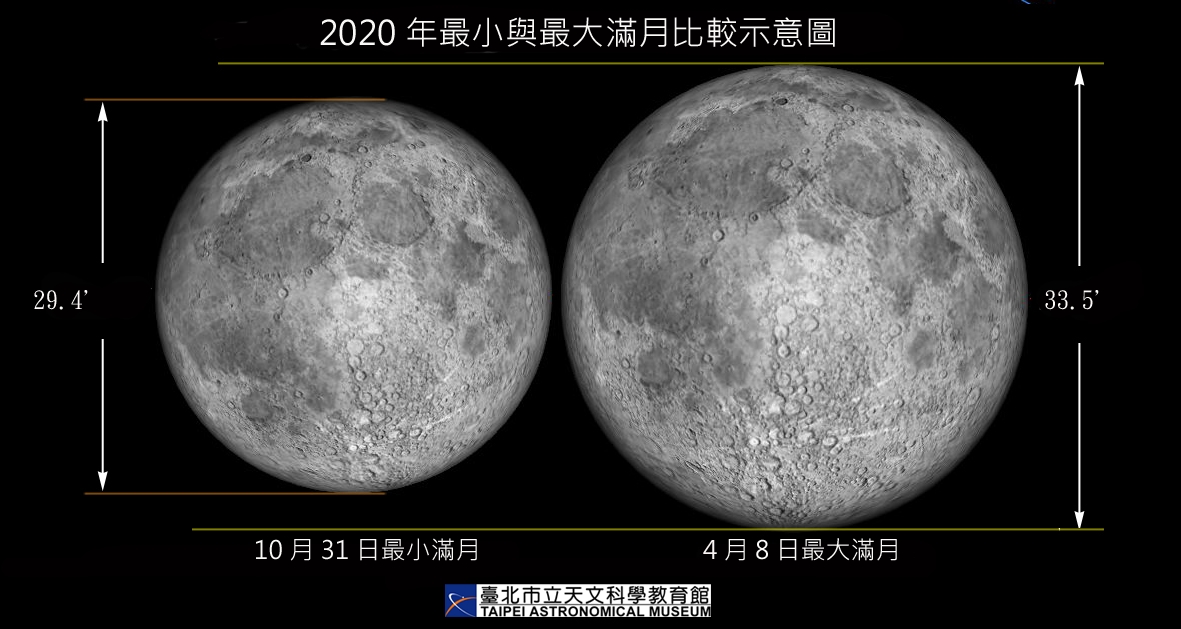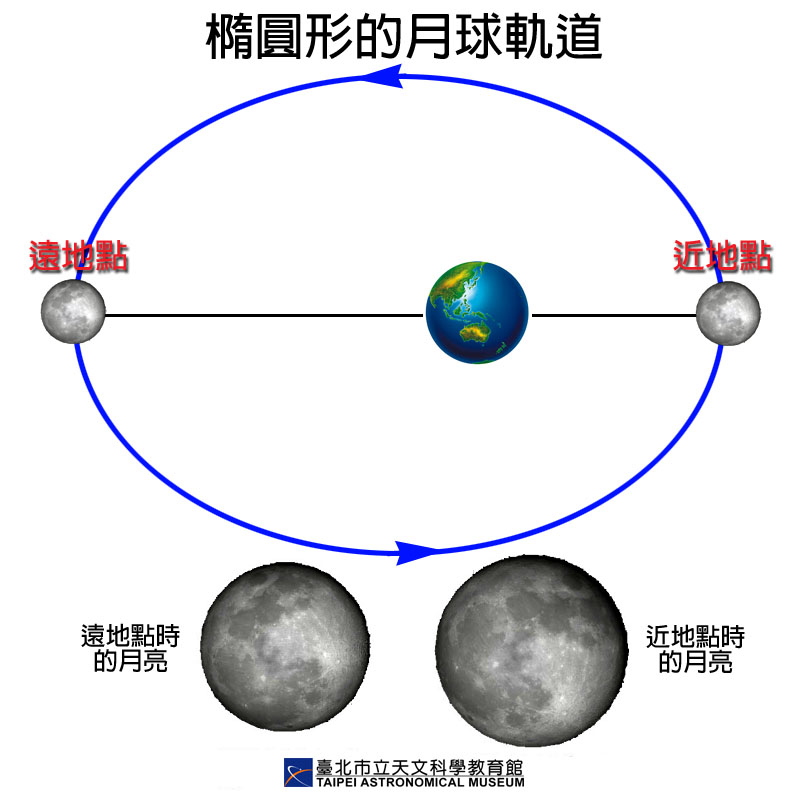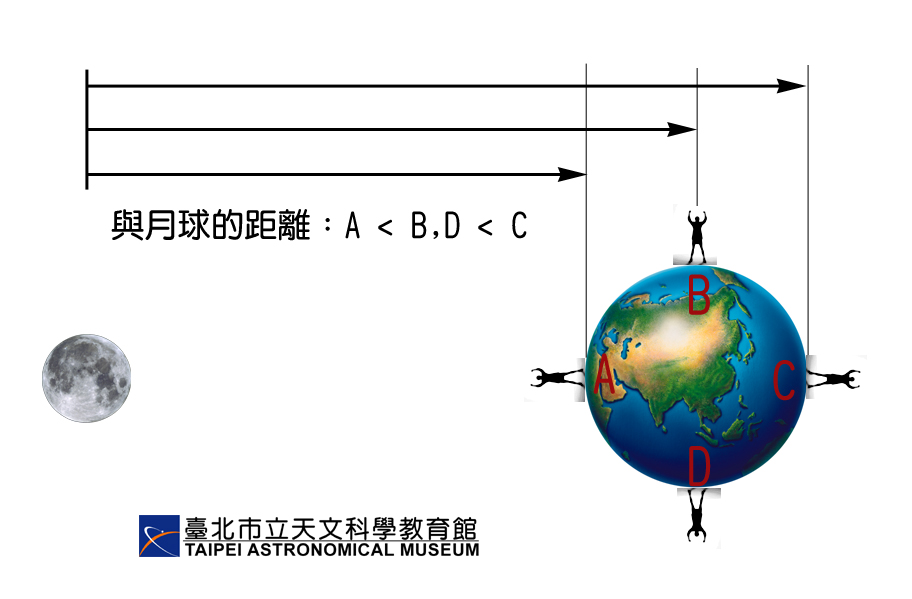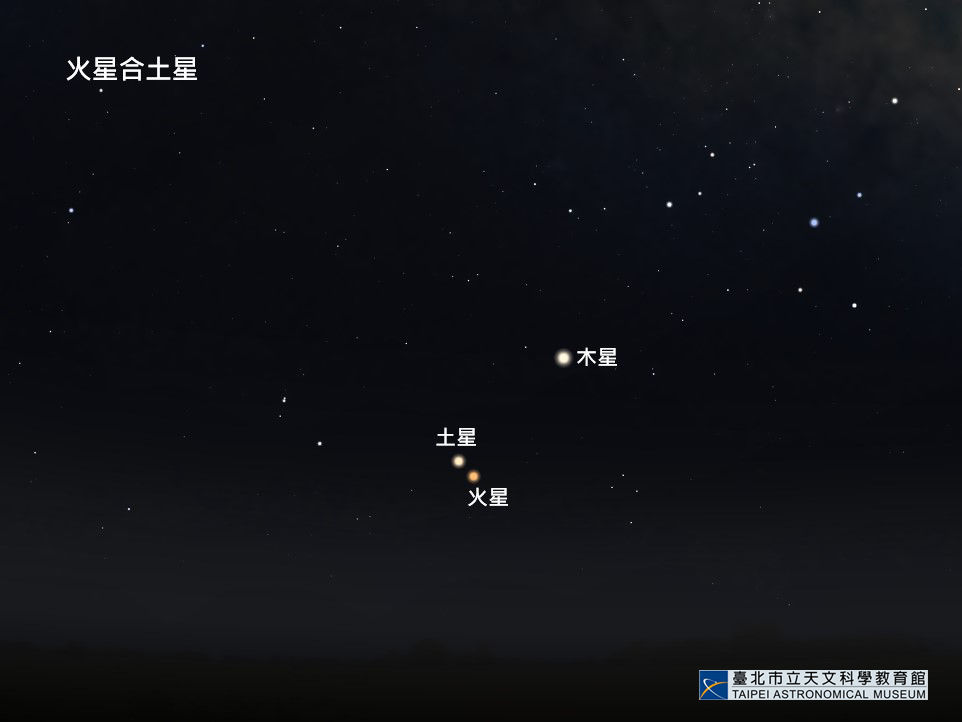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乡达普村,有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天文台。每年,当太阳光透过测孔楼顶的日光出孔照到测光石,三点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就到了春耕及灌溉的时间了,一年仅出现一次,精准程度等同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这座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天文台,背后折射出的是西藏天文历算学历经千百年发展变迁的真实写照。
西藏天文历算学是通过对宇宙星体的运转以及对季节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并推算出一年的年月日时,预测各种星体位置的一门独特的自然学科,是藏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进行交流,通过上观天文、下查地理得到的智慧结晶,不仅涉及藏医学,还涉及依据天文历算学原理推算出的各地适宜的农耕牧作时机、物候、节令等与广大农牧民息息相关的特殊领域,特别是中长短期天气预报等气象学,辐射多个相关科学领域。
“前世”
达普天文观测台,由测孔楼和测光石两个部分组成。在测孔楼的西墙面南北方位165度至345度的位置,西墙正中间的屋顶上方有一个日光出口,而测光石与测光孔西墙的距离为29米,观测石周围还附建了十二宫二十七宿原文造型大理石保护圈,“当太阳光透过测孔楼顶的日光出孔照到测光石,三点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就到了春耕及灌溉的时间了,这种方法村民们已经沿用了几百年。”达普村村民次仁桑布告诉记者。50岁的次仁桑布从小在达普村长大,“小时候不懂事,总觉得这太过于神奇,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直到后来自己种地的时候,才发现这座天文观测台的意义。”次仁桑布感叹不已,“我们家种植了20多亩地的农作物,每年春耕春播之前都在等待达普天文台给我们‘发信号’。”
什么时候耕种最佳,什么时候收获较多,什么时候上山采药,甚至什么时候出现日食、月食、地震,西藏天文历算学都能给出精准答案。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西藏天文历算学的“前世”,记者专访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基础部天文历算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普琼次仁。
“西藏的天文历算肯定与迷信有关,不就是蛊惑人心的‘变种’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公众因为不够深入的了解,对西藏天文历算学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误区。普琼次仁介绍,西藏天文历算学有着3800多年的历史,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就出现了天文历算学,后来随着吐蕃王朝时期藏文化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学习和研究天文历算的学者。文成公主入藏时,将内地的部分天文历算学知识带到了西藏;后来金城公主又将内地的医学和算学方面的内容也传播到了西藏,融入到了西藏天文历算学系统中;之后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挑选专人赴内地学习五行历算,直至公元1027年印度的《时轮经》传至西藏并完全翻译成藏文,从此,西藏天文历算学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系统的天文历算体系。”普琼次仁告诉记者,“后来的13、14、15世纪,佛学、医学、历算学融会贯通,使得西藏天文历算学迎来了最为发达的时期。”
“公众之所以对西藏天文历算有诸多认知误区,很多是因为在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天文历算学更多地只能在寺庙传承,当时只有寺庙具备这样的学习、实习、推广条件。”普琼次仁说。1989年,西藏藏医药大学的前身西藏藏医学院成立,时至今日,西藏天文历算学一直在保护中传承。
西藏天文历算的“前世”,承载的是藏汉民族团结千百年来的不朽记忆,以其为代表的藏文化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今生”
月食、日食这些天文奇观总会引发诸多关注,想要如约观测到这些,则需要精准的预测。“众所周知,月食、日食这些天文现象出现之前,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电视台都会报道,这些往往是基于内地天文台或西方天文历算,比如位于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就承担着我国的日月食预报工作。根据西藏天文历算学,我们综合研究发现,月食预测的精准度达到了100%,日食预测的精准度也达到了100%,间接辅证了西藏天文历算学的科学性。”普琼次仁告诉记者。
在西藏民间尤其是在农牧民群众家里,往往都备着一本名为《西藏天文气象历书》的书籍,书中涵盖年历、月历、日历,何时注重防灾(旱涝)、何时适合耕种等。“记得在书中有一幅农民牵牛耕种的画面——《春牛图》,农民的裤管是否卷起、牛尾巴甩向哪边,都是西藏天文历算告诉我们农事活动中的注意事项。”次仁桑布告诉记者,“老百姓信这个,我想更多还是因为西藏天文历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西藏藏医药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水晶球”体的建筑分外引人注目,这个非同寻常的“水晶球”其实就是该校的天文观测台,“这个球体建筑内部的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月球、太阳、金星等,通过现代科技观测,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太空世界。”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次仁卓嘎告诉记者,“有一次在观测的时候,我发现月球的表面像是冰块一样,感觉书籍的知识和真实的观测多少还是存在区别的。”除了天文观测台,西藏藏医药大学还有独立的手机APP软件,包含藏历书、教程等,“我的老家在尼木县塔荣镇,家里有12亩地,小时候就常常看到母亲通过天文历算书查看农时,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好奇,后来觉得西藏天文历算学真的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所以后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西藏藏医药大学的天文历算学专业。”说这话的是西藏藏医药大学教师德吉卓嘎,采访见到她时,她正和普琼次仁主任用沙盘做着计算,“沙盘是西藏天文历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起来又快又准。”作为西藏藏医药大学首批西藏天文历算学的本科生,德吉卓嘎从对于天文历算的懵懂、喜欢、追逐,转为现在的学习、思考、传播,文化背后持续的、深沉的力量在感动着她。
如今,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藏天文历算,“今生”正在获“新生”。
记者手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古象雄到吐蕃时期再到明清两朝直到当代,西藏天文历算学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时代精彩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从祖国内地到青藏高原到传入的印度文明,我们看到的是西藏天文历算学发展进程中的融会贯通、取精华去糟粕的生动实践;从西藏天文历算学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对其保护的决心,让一批又一批人有了“守望”的勇气和坚持。诚然:西藏天文历算学是民族的,更是国家的、世界的。
(摘自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拉萨日报》内页第2版,记者:扎西平措、孙靖宇)


★★